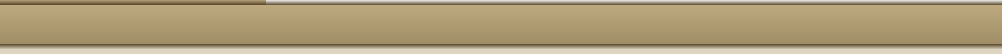倒不是年龄歧视。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运营公司总经理刚好解释,因申请者众多,不得不作筛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涌入景德镇。在这座古老瓷都里,大大小小的集市、创业工作室园区,甚至街头巷尾,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据2023年统计,过去10年景德镇人口呈净流入趋势,目前“景漂”已超过6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中部四线城市大多呈现人口净流出的趋势。
2010年前后,“景漂”一词开始伴随着“北漂”“沪漂”共同兴起。不同于在超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在景德镇,“漂”的人群更为集中:20世纪90年代来学艺的工匠、毕业于全国各地美术学院的年轻学生,以及海内外艺术行业创业者成为“景漂”的主要人群。但“漂”的生活并非千篇一律。有人轻松自在地旅居休闲,有人日夜兼程为创业奋斗。相比于短时间内流量的涌入,这座江西小城始终活跃在年轻人向往的生活目的地榜单上。
年轻人向往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到景德镇,观察年轻人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话,并尝试回答他们留在一座小城的理由。
队伍里清一色的年轻人,拉着拖箱、行李箱、背着大包。不明所以的游客凑上去,以为又是某处网红打卡点,毕竟在现在的景德镇为拍照而排队的情形并不鲜见。问了队伍当中的人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市集的摊主,在等待领取摆摊统一规制的桌椅。
时间一到,仓库的门被打开,年轻的摊主们依次进入。“景漂”嘉佑挑选后,把带来的两筐作品连同摆摊用的桌椅,一同放进露营小推车中,不停歇地朝着摊位走。摆摊的具体位置凭抽签取得,嘉佑这周运气不错,还在主道上。
嘉佑的摊位展示的是手工烧制的香薰。和前几周摆摊时不同,这天,他特意带了几个复古式的置物架和一块印花布料,为的是把产品放得更加错落有致。“摆得不好看会被说”,嘉佑说,上周因为桌面摆得过满,陶溪川的市集巡查员对他提出“警告”。
“一定得是原创。”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运营公司总经理刚好解释,陶溪川的摊主申请摊位时除了递交基本信息资料,创新性和产品风格评选也要交给从摊主中挑选出的志愿者互评。
蒙古族小伙满都拉记得,来景德镇的第五个月,他第一次入选摆摊,带着大包小包蒙古族传统纹样的陶瓷酒杯、咖啡杯、盖碗、果盘,在集市上显得稀奇,第一晚就卖出了三四个。
他现在的摊位在陶溪川的白色帐篷,是设计师片区,作品也被保管在专门区域。比起其他区域,设计师片区的展陈自由度最大,不再是固定的方桌,也可以放大尺寸的道具,唯一的宗旨是好看,“要个性化出来,个人风格要很明显”。
“我们平时也会去创意区溜达一下,如果说经常看到他(摊主)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可能会让这个摊主先暂时回去调整一下。”一位参与过摊主筛选的志愿者说。
天色渐暗,陶溪川里的老厂房、红砖墙、高耸的窑炉烟囱被昏黄的灯带勾勒得更具线条的美感,提醒着这座城市过去的制瓷记忆。
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景德镇曾经历过一次行业低谷。随着国营陶瓷厂的改制,大量的陶瓷工匠离开这座城市,另谋生路。好在独有的手工艺基础并未丢失,也逐渐吸引来数以万计的艺术“景漂”。此后,街区开始重建。如今的陶溪川街区,就是在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宇宙瓷厂”的旧厂房原址上改建。陶瓷匠人们回归,加上年轻人涌入,给这座小城增添不少新意。
2005年香港艺术家郑祎创办乐天陶社在雕塑瓷厂正式开张营业。三年后,一些做陶瓷的年轻人向郑祎建议,是否可以在乐天咖啡厅门前的空地摆摊。本地人江智徽当时在雕塑瓷厂租了一间40平方米的工作室,他记得最常光顾的客人是松鼠和野猫。可没想到,工作室对面的乐天创意市集就从地摊起步,一点一点做出了影响力。现在,数十个市集在景德镇相继开花,成为现在景德镇重要的城市名片。
陶溪川外的马路上,车流正变得缓慢,游客们不断涌进来:穿校服、背书包的中学生,戴头巾身着文艺长裙的姐妹团,正在为一款手握杯讲价的北方客人……在陶溪川,不仅摊主,流连其间的客人也大多是年轻人。
在多数人看来,历经千年积淀、完整而成熟的陶瓷产业链,门槛极低的创业环境和舒适自在的生活氛围,是景德镇吸引年轻人的理由。
2022年春天,26岁的满都拉辞掉了武汉陶艺老师的工作,带着不到一万元的积蓄来到景德镇。
虽然大学也是陶瓷雕塑专业,但因为学校地处西北,做陶瓷有着不少局限。在景德镇,满都拉把画好的器型设计稿交给本地工匠,对方负责提供坯体,他则在这些陶瓷上实现自己的艺术表达。
摆摊的第一个月,满都拉赚了三千多元,完全达到了预期。在过去两年,满都拉还参加过三次规格更高的陶然集,在陶溪川办过展览。最近,他打算在作品中做些新的尝试。
陈圣兵同样是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大学时期,他要做一件陶瓷作品,需要一个人要包干整个过程,从上山挖石头、粉碎后做成泥巴这一步开始。“因为我们没有景德镇这么多师傅,没有人拉坯、也没有人手绘。”大二时,陈圣兵就定下目标,毕业后一定要来景德镇发展。
2022年7月,毕业后的陈圣兵带着家里人支持的2万元南下。在著名的雕塑瓷厂附近,他租了一间工作室,加上住的房子,两处房租每月只需1300元。
陈圣兵把在景德镇创业的景漂粗略地分为两类人:一部分年轻人是“来玩的”,可能一个月赚5000元,花4000元;还有一些真正有创业计划的人,仍然在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努力。
“最开始在三宝村让我非常震撼,小小的村落中,聚集了大批做陶瓷的人,很有匠人精神的氛围。”2019年来景德镇旅游时,高伟豪被这里深深吸引。
贵州大学雕塑系毕业的高伟豪在三宝村向许多人请教,学习做陶的手艺。时间久了,只是背旅行包来旅游的高伟豪醉心于陶瓷制作。逐渐摸清了做陶瓷的工序、方法和手艺后,高伟豪也意识到,这个有着72道复杂工序的陶瓷产业无法独自完成。
他决定留在景德镇。在湘湖租下一套农舍后,高伟豪开始为实现自己脑海中的创新仿古瓷创业。
在景德镇,像高伟豪这样,从游客就地转为“景漂”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高伟豪现在的助手是个来自山西的00后,原本学的是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也是在一次旅游后留了下来。
小红书上,司琪是一位有七千多粉丝的陶瓷创作者,她有500人的微信社群,小红书上的第四个群聊也将近满员。她的产出不多,不参加线下摆摊,也不供货给买手店,每月制作40多个手捏杯,一上架就被抢空,没抢到顾客还会发来五百字的求购小作文。
司琪从未学过绘画,硕士毕业后她去杭州做了销售类的工作,那一年里,业绩、考核,压得她无法喘息。“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能再这样一直上班,”前年夏天,她决定裸辞,漂到四线城市景德镇。
做景漂前,她专程来景德镇上过两回雕塑课和陶艺手捏课。租工作室、报陶瓷课程、租公寓……来景德镇一个月,积蓄已经用了大半。出于对经济的恐慌,司琪先找了一份民宿的前台工作。夜班,一个月工资2000元。她还把租下的两居室当中的一间客房做成民宿短租了出去。
“没有做产品之前,我就是混吃等死,随便捏一捏。”初来景德镇,司琪找不到方向,她召集过一个小规模市集,却有些无厘头地在市集上卖烤肠。
直到去年7月,司琪才有了灵感,设计制作一款黑色植物线条的咖啡杯在小红书获得了几千点赞,成为爆款。
“景漂群体中有一大部分人是在经历令人失望的一、二线城市生活之后,反向流入景德镇的。我理解很多人在原来的轨道上过得很不开心,他们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最近五年,做景德镇城市品牌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传播学博士周洁(化名)来过景德镇六七次,也陆续访谈过几十位景漂。
周洁观察到,相比城市里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制度,生活在景德镇的人们有一套自己的时间观,“景漂”们也能够在这里实现一种时间自主性强的生活。
“最吸引他们的,还有这里有一群跟他一样‘奇形怪状’的人。”不少“景漂”告诉周洁,景德镇的“瓷力”在于,在这里容易交到朋友:学陶瓷的培训班上会认识同学,集市上有一起摆摊的朋友……一群有相似追求的人,天然更有共同话题。满都拉已经连续两年留在景德镇,和认识的朋友一起过春节。
裸辞、逃离大城市、跨界、松弛、随性,司琪的故事标签似乎符合人们对“景漂”的想象。有人称景德镇是“平替版大理”,有着两地生活经验的司琪却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景德镇的另一面是竞争、淘汰和辛酸。
40的高温天里,在没有空调的10m城中村单间,一位漂了5个月男生对着视频教程练习汾水的场景一直留在周洁的脑海中。
景漂到了第三个年头,满都拉觉得自己才稍稍放平心态。“去年,我一天不干活,就会觉得好愧疚。每天都要通宵。”满都拉说,初到景德镇时,他充满迷茫,“我只知道自己喜欢民族题材,想画出来。”头几个月,除了外出散步,大部分时间,满都拉把自己关在屋里,每天练习在胚体画画。
一起做“景漂”的大学好友,比满都拉更早申请去市集摆摊,2022年的五一小长假却只卖出一单小雕塑。没有收入,加上不被认可,同学放弃景漂回了内蒙古老家,如今在放牧。满都拉最近聘请了一位兼职画师,那是一个和他同年毕业、学视觉传达的女孩。女孩来景德镇也想做工作室,但苦于没有本金,对陶瓷也缺乏了解,只能先从兼职起步。
“在景德镇没有事情做,你会觉得很无聊。表面看起来他们在躺着,其实可卷了。”司琪讲述了另一种说,一般朋友们下午聚会完毕后,晚上回到各自的工作室,开始干活。
相较于提升陶瓷技艺,并非科班出身的司琪更擅长发挥原本的销售优势。她特意设计过自己的产品包装,想让客户感受到自己的用心,“我不是学艺术的,卷不过产品,只能卷包装了。”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在高温和时间的双重炙烤下,烧瓷稍不留神就会失败。烧成一陶瓷器皿,乍一看没有明显瑕疵的比例在80%到90%,但如果经过专业的质检,真正成品率要更低一些。
对高伟豪来说,每次开窑都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窑开了以后不满意,只能拿锤子咔咔一顿砸。”高伟豪最崩溃的一次,满怀期待开窑,结果一窑400个杯子里有300多个要砸掉。
高伟豪记不清有多少次面对一地碎片,想要放弃。但有时候,哪怕有一个杯子烧制成理想状态,又会让他打消念头。
陶瓷的魅力,或许源于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前期投入了多少心血和时间,精心地拉坯、修坯、绘画、雕刻、上釉,最终仍须往窑里一放,等待命运的馈赠。这种“赌”的成分,天然地吸引着高伟豪,“这就是它好玩的地方嘛。”
创业初期,高伟豪每年给自己设计的创意产品投入80万元左右,“如果盯着钱去做,做不出来什么好东西。在景德镇,师傅们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去实现,怎么画,怎么上釉,最终成为一个产品去售卖,这种参与程度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在景德镇,几乎每个做陶瓷的人,自己手中用的都是瑕疵品,它或许只是有一个黑点、一个气泡,并不影响使用,但绝不能售卖。这恰恰是手工陶瓷的哲学,永远无法标准化量产。
在一次次拜访中,周洁也逐渐确信年轻人钟情景德镇的理由——传统手工业有“付出就有回报”的确定感,而手作陶瓷又有做艺术的不确定感。“这种类似传统手工业却又完全不同的手作生产和生活方式给了他们多样的选择,自然也就成了理想的试验场。”
“景德镇试错成本非常低,可以不断去试错,不断修正你的人生方向,不断地来设定你的作品。”景漂10年的纪录片导演姚飞如此总结自己的观察,“仿古陶瓷有仿古瓷的受众,刚学会,拉坯也没拉好的,烧出来属于陶艺作品。你做成什么样,都有人喜欢。市场宽度、广度都有。”
无论是跌跌撞撞最终被流量砸中,闯出一条路,还是不计回报地投入,以获得商业利润之外获得自我实现,景德镇的年轻人们似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最近一次在景德镇做课题调研时,周洁正临近毕业,她要做出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老家谋一份教职。“我挺排斥大城市的快节奏和高竞争的压力,很想回到家乡,但我回了家又会失望,因为在家里看不到多少年轻人,没有多少活力。”
周洁觉得,景德镇完美地结合了两者:有四线城市的悠闲,也不觉得和在北京、上海的同龄人脱节。
嘉佑做过销售,也进过厂,来景德镇学了两年手捏,现在卖的是在各类市集上还算热门的香薰,但他更长远的目标是做手工拉坯的茶具,“我得先生存下来,才能把事情做好。”
疫情之后,许多原本离开的匠人再次回到景德镇,加上新加入的年轻人,景漂的人数还在飙升,房租也随之翻倍。
“不止房租了,做陈设的二手家具全都在涨价。”满都拉随手指了指客厅的斗柜,“这个柜子去年120元,现在得两三百。”
陈圣兵记得,他两年前租的工作室,原本400元月租都没人租,今年已经涨到了每月3000元,还是会被立刻租掉。2024年,陈圣兵把制作场地搬到了相对偏僻的农村,“一年的租金是28000元。”
景德镇还在变得更加网红,今年“五一”假期前三天,景德镇市累计接待游客量突破300万人次。对于身处其中的创作者而言,也有困扰。
在社交媒体“没有人能空手离开景德镇”的话题下,不少游客晒出手臂戴满手串的图片,大呼“在景德镇实现手串自由”。纪录片导演姚飞专门去陶阳新村集市观察过,休息日晚上,一个摊位10分钟能卖出400元的手串。
在景德镇的陶瓷手艺人当中,有人觉得十元三元串的陶瓷手串撬开了景德镇文旅大市场,给城市带来了流量,有的作者则直言不讳地批判,“景德镇毕竟是靠传统手工艺,到处的十元三串让人感觉像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
作为陶溪川的运营方,街区内不止一家商户向刚好反映对街区人流量过载的担忧,“人流量10万人的时候还不如6万人,他的销量、体验感都会变差。”但刚好认为景德镇的火热流量终归会回到正常的平衡。
“年轻人多,这可能是很多城市羡慕景德镇的地方。”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运营公司总经理刚好笑着说。古老的城市需要年轻的力量来激活,陶溪川从2015年就提出要为年轻的艺术家、设计师以及手艺人去提供创业创作的场所。刚好记得,陶溪川第一批的商业业态中,没有一家江西土菜馆,全都是日料、韩餐,西餐,还有有咖啡馆有健身房,“一切城市生活配套都围绕着年轻人。”从初级的集市练摊,到入驻邑空间商城、直播基地,再到陶瓷智造工坊,陶溪川扮演着青年创业扶持者的角色,在满足创业者不同阶段的发展。
陶溪川创意集市日益火爆,陈圣兵申请了好几次都没能入选。不得已,他将主要销售渠道放在了电商平台淘宝上,销量喜人,常常是“出一窑卖一窑”。擅长运营新媒体的陈圣兵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分发自己的制作内容,积累了不少粉丝。
没过多久,青蛙勺在淘宝举办的“丑东西大赛”上意外夺魁,陈圣兵还专程杭州领了奖。陈圣兵至今不知道是谁替他申请了这个有些无厘头的奖项,但这件事让陈圣兵的产品收获了空前的销量。
为了接住新一波的流量,他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召集了自己的学妹组建了一个4人团队,雇了村里的阿姨来帮忙打下手,换了更大的窑,生产场地也扩大了一倍,尽可能地加快生产速度。
“我们这个行当就像中医,主要依靠经验,越老越值钱。”陈圣兵觉得自己大概率会一辈子做陶瓷,他仍然坚持不断开发新品,“吃老本早晚有一天会倒闭,这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了,只有保证一直更新才会有活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二级市场,让作者的知名度更高,产品才会有升值空间。”
关于未来,虽然没有想好是否把家安在景德镇,但陈圣兵确定的是,工作室一定会固定在景德镇。“这个城市本身就是最大的影响力,发货地址是景德镇,这一条就足够有市场竞争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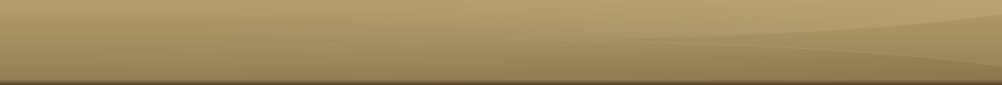
![首页-[焦点平台]-焦点注册陶瓷平台](/picture/1524329934.jpg)